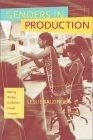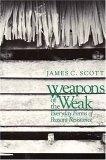Escobar的這本書雖說因為我對發展理論以及發展和依賴理論之間的脈絡的不甚熟悉,因此暫時無法定位這本書。不過光就整本書中豐富的內容和有利的論證,應該都足以讓這本書在整個論辯中佔有一席之地。Escobar本書主要想要探問發展作為一種論述,最早是在戰後出現的一種油全球的菁英和權力核心者所共享的進步概念,然後從這個進步概念擴及到全球希望能夠分享進步的果實。於是在這個夢想的號召之下,在第三世界執行著各種以經濟成長為目的的發展計畫,最後卻讓這個菁英的夢想成了第三世界人民的惡夢。在這個過程中,發展和進步的夢想不只沒有兌現,卻造成了許多的未發展和赤貧,以及隱形的剝削和壓迫。本書之中,作者分別從被問題化的貧窮、經濟發展和成長、食物和饑荒、權力和可視性等幾個主題來探討發展作為一種論述在過去辦個多世紀以來對於全球的衝擊和影響。
Escobar指出,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以米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除了智利於復甦歐洲經濟之外,為了要防堵共產勢力的擴張,因此將其視野投向了第三世界。於是,他們突然發現了充斥於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貧窮。而這個突然被發現的貧窮問題就吹起了重塑全球經濟和政治權力結構的號角。發展的種種計畫在初期就是打著消滅貧窮為口號進軍第三世界國家。Escobar點出了辦個多世紀以來影響著發展論述的各種元素;比如說30年代經濟大蕭條之後風行米國的凱因斯學派提供了政府、國際權力干涉經濟發展的思想基礎。對於共產主義擴張的恐懼則促使了發展計畫往往傾向於強調個人和市場的獨立連結而忽略了社群發展的可能性。依附在地方父權既存體系下執行的發展計畫則抹除了女性在經濟生產中長期以來的存在和既有的位置。而以西方中心主義為出發點的各種發展計畫一旦進入了第三世界國家則往往強迫當地人接受西方的價值觀。
Escobar認為,這種種的面向來看發展論述時,我們就會發現其實發展這概念本身並不是什麼全新的東西而只是把既存的舊元素重組之後的成品。除此之外,從上面的描述中也可以清楚的看見,發展論述本身是一個文化性的組合。不過這種文化性的組合在科技詞彙和科學知識的包裝下成為一個將其文化元素引強起來的、中性且客觀中立的,並且是「追求第三世界人民福祉」的一套論述。透過將第三世界及其人民納入專業知識和西方科學的研究中,除了發現了普遍存在的貧窮現象並且將之問題化之後交給技術部門如經濟學家來處理。這個將第三世界專業知識化的過程排除了政治和文化上的干擾而成為純粹中性的科學問題。在這個被知識化的過程中,第三世界被磨塑唯一個和西方不同的,處於多種問題交織的狀態,而唯有透過經濟發展才能夠蛻變並且擺脫種種磨難的他者。
這種透過發展才能改善落後的信念成了整個發展論述的機數,同時Escobar指出,即使幾乎每個十年左右,發展論述的內容都會發生某種程度的改變,但是即使是這樣,這整個基本的框架一直到現在也不曾真正的改變過。舉例來說,即使是從凱因斯學派的干涉主義到復甦了的新古典/新自由主義強調的完全競爭和放任自由市場這種光譜極端的典範轉移,也都不曾真的影響過整個發展論述的框架。也就是說,關於遇到問題之後如何解決的看法可能會隨著時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是透過發展來解決問題卻是無庸置疑的。這個框架的背後則同時也包含了一種「只有西方的科學知識是拯救是人免於苦難的唯一真理道路」的觀點。
而我們也可以在綠色革命或者環境保護這兩個不同的議題中看出這種傾向。雖說各家標準不一,因此這個世界有10-15%或者三分之二的人處於饑饉之中。但不管怎麼樣,饑荒的問題需要被解決,而解決的方式就是來自西方的現代化農業,如機耕、化肥,僅可能的提供鄉民產能以銷售於市場等等。於是,西方再次的發現了新的問題,並且透過世銀去之行解決問題的計畫。不過,很快的我們就會發現,這些計畫背後的另外一個目的則是透過農業現代話來生產大量便宜的食物以供給給城市裡面的無產階級和其他的工業區塊。也就是說,綠色革命真正服務的對象並不是饑饉中的人們而是國家的經濟成長。
Escobar更進一步指出,綠色革命不只沒能解決饑荒的問題,相反地,因為發展的成果分配不同,導致大量的小農不只被迫退出原本的生計農作,有些比較不幸的甚至還被逐出土地成為無產階級。再一次的,西方的發展專家們往往在實際下鄉前(其實作者深深的懷疑這些搭乘頭等艙住五星級飯店的世銀幹員們是不是真的有下鄉)就已經自認十足的了解問題並且有完整有效的解藥了!而這解藥一定有用,「因為我們已經在西方實際驗證過了!」
這兒也可以稍微跳出來討論一下發展對於鄉民社會的認識。大致上來說,鄉民長期以來被視為非理性、無知且守舊的保守人群。但是作者認為一定程度上這只是因為鄉民社會原先呈現的圖像並不是這些發展專家們所熟悉的ㄋ阿種特定的知識類型。而專家們又只相信這一特定的知識類型和其典範下生產出的知識,於是處理鄉民社會的方式就變成要不就是改造他們,史他們成為在這個典範下可被認識的對象。而在發展過程中成功被改造的那些小農們會成為樂於擁抱市場的商人,至於那些失敗的人口則會被是為「剩餘人口」而最終會被蓬勃發展的經濟(如果有的話)所吸收。亦即,無產階級化。而不管怎麼樣,在發展論述的指導下,綠色革命就像一個西方權威父親無私的教誨無知的第三世界小孩怎麼讓自己吃飽的計畫。
這樣的父權結構在發展論述中,不只不是該被消除的對象,相反地,還是發展論述依附其上以求計畫得以順利施行的原因。作者指出,除了第三世界女性一開始在發展論述中缺席,之後則是只被當成繁衍後代的存在,然後是個生產和在生產者。不論是哪一個時期的對於女性的認識,都是一種剝除了女性主體性之後的工具性存在。另一方面,西方的女性主義者也已自身的問題當做是第三世界女性的問題並且希望提供協助。換言之,這套女權意識的進路和發展論述的思維如出一轍。Escobar認為,這根本就是女性主義指導下生產出的知識為父權架構所收編並且為了鞏固父系霸權而服務。
總之,Escobar的這本書,我認為他是雜揉了Foucault關於論述、知識和權力的討論,以及Saide的東方主義來討論發展的。他的進路大致上是服膺了 Foucault的看法,當一個對象被納入了知識論述之中並且被系統性的認識之後,這對象就在這個知識體系中具有可視性;而一旦成為可見物,那就成了權力監控、凝視和管理的對象。而以西方的科學知識體系來觀看第三世界則呈現出一種東方主義式的色彩,亦即,這個可視的第三世界視特定的凝視角度下的第三世界,和真實的第三世界未必真的那麼有關係。而在Escobar的認識中,發展的論述就是建基在這樣的立場上持續的創造出發展的計畫。而這種特定的凝視角度,也是為何全球菁英眼中的理想成為第三世界人民的惡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