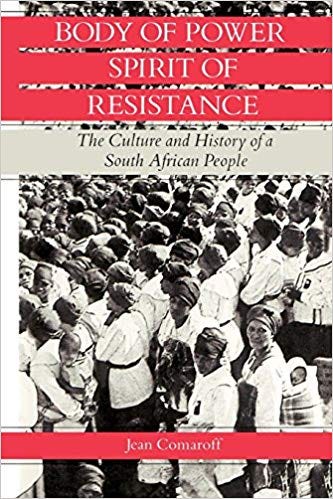李靜君在這本書中討論了在香港和深圳兩間由同家港資公司所經營的工廠中的勞動控制和治理至(factory regime)。她指出,這兩間工廠所處的地理位置不遠,因此基本上由同一批經理人在管理,同時因為不論是在英殖香港或社會主義中國下的地方政府對於工廠的態度基本上是採取放任主義且不會有太多的干涉和介入。在這種國家不介入且不提供工人足夠支持的狀況下,如果依照Burawoy的看法,在工廠的內部必然會生成專制體制。但在李的兩個工廠案例中,只有深圳廠形成了專制體制,而香港廠則是截然不同的霸權制度。基於外在政治社會環境類似,且是由同樣的高層管理,結果卻在兩個工廠內形成截然不同的工廠體制而和Burawoy對工廠體制的討論不盡相同,這使得李試著去探問,是什麼因素形構了這兩間工廠內的工廠體制?
李認為,Burawoy以階級為基礎的討論「生產的政治」(Politics of Production)的確開創了一條新的取徑,幫助我們看到了勞動過程(labor process, 生產裡任務所需具備的技術和社會組織)和生產機器(production apparatuses, 規範和磨塑工作現場政治的機構),並佐歷史材料的比較而創造出工廠體制這個可以連結階級宰制中微觀和宏觀層面的概念。這使得Burawoy可以把工廠內的勞動過程和工廠外的國家制度、工會力量等等連結起來,從來形成了對專制和霸權體制的區別,而這是過去勞動過程理論的研究者們所不曾注意到的差異。
不過,即使是Burawoy的理論具有如此的開創性,但是李批評說,Burawoy過於強調階級的重要性,因此對於理解女工的狀況幫助其實不大。相較於男工,女工更難仰賴國家或者企業的力量去得到再生產其勞動力所需的資源,而必須仰賴地方性的人際網絡或者親屬和家庭連帶中所能取得的資源。這些組織和資源取的方式,都是來自於性別化的組織且內化在地方的勞動市場中。李因此認為,正是這些不同的勞動市場特徵,決定了兩個工廠中的治理體制的差異。因此,李主張,在探討工廠體制的時候,必須加入性別的層面。
李進一步的引伸,女性主義者指出過去的馬克思主義者或者Burawoy本人都忽略了階級宰制中性別所扮演的角色。女性在工作的場域中從未缺席,而往往是被當作產業預備軍而成為階級宰制中的一環。女性主義者指出了這一點並且將性別的面向帶入到關於工作的討論中,從而造成了典範的轉移,並且提醒了我們性別時常被用來作為勞動控制的一環,同時也是在意識形態、組織和認同這三個層面中運作的權力過程。不過,當性別也是權力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因子的同時,這樣的性別也受到了社會、政治機構的塑造。由此,女性主義學者將性別帶入了工作的討論中,並且使性別在勞動過程中成為重要的一個環節。
接著,李則是指出了在香港和深圳基於勞動市場的差異性而在廠內生成不同的工廠體制。香港廠中形成了家族主義式霸權體制(familial hegemonic regime),而在深圳廠則形成地方主義式專制體制(localistic despotic regime)。在香港的家族主義霸權體制中,李指出這些多半已為人母的女工們之所以願意留在香港已經屬於夕陽產業的製造業工廠中繼續工作的原因,是因為Liton這間工廠的工作時間安排使得女工們可以同時兼顧全職工作和照顧家庭的需求。這些為人母的女工不僅以可以好好照顧家庭,培養後代使之衣食無缺平安長大作為其定義自身女性認同的主要元素,同時也是正當化自身辛勞的主要支撐。而Liton的管理階層所採取的「人性化」管理策略和措施,比如說允許女工因突發事故中離而不扣薪水不扣缺勤,以及其他使女工得以兼顧家庭的工時安排,這些都使得女工們心甘情願的捨棄更高的薪資,留在Liton成為長期穩定的、流動率超低的員工組成。換言之,在香港Liton中,藉由融入了家族主義的勞動控制政策,使得香港廠擁有一批穩定、經驗老到且樂於和經理合作的一線員工。而這些女工也因為對於Liton的工作安排感到滿意因此會自律的不打破這些為了可以滿足家庭照顧需求而得到的福利,並且自願順服於工廠的管理之下。由此,構成了李所謂的家族主義式的霸權體制。
而深圳廠的狀態則迥異於香港,Liton在改革開放之後前進深圳,並在當地雇用了大量的農民工入廠工作。這些「打工妹」除了在地粵籍或者福建的工人之外,也有為數不少來自中國數各北方或者更內陸的省分。不管是來自哪一個省分,這些農民工的移動軌跡,多半都是先有「老鄉」在Liton工廠內中做,能夠從工廠得知內部的聘僱消息,然後把這些消息傳回家鄉,讓家鄉中有意外出工作的女性們可以在恰當的時機前來應徵。因此,工廠中的勞動力再生產,是循著地方主義的路徑去建築。而在勞動控制上,則是藉由提拔來自某一省分的男性成為領班,以這些男性在漢人父權社會中既有的權威位置去控制其他來自同鄉的女性勞動者。除此之外,由於這些「打工妹」多是年輕女性,因此外出打工時,即便不純然是接受了家戶經濟需求的安排而缺乏煮體性的慾望動機的結果;但年輕女工們依然要和父系威權得到妥協,在有同鄉工作的工廠中工作,即是這種妥協下的產物。一來年輕女工們被託付給同鄉親族長輩照顧和就近監視;二來工廠被視為是一個有紀律、性別界線分明、不用拋頭露臉而合適年輕女性並且不會損及其婚前名聲的工作場合。由此,使得廠內的勞動控制得以依循著李所謂的家族主義式的專制體制開展。
除了建構和鋪陳兩地勞動市場的差異對於工廠體制的影響之外,李同時也以另一組概念「打工妹」(maiden workers)和「主婦工」(matron workers)比對兩地女工特質上的阿易。「打工妹」常被用來指稱深圳的女工,對於這些女民工來說,工廠工作只是命中的一個暫時性的階段,是滿足未來人生規劃的經濟基礎。而香港這邊的「主婦工」則通常是年紀稍長,有家室小孩的工人。這兩種不同的形象說明了女工本身也會因為自身的利益、需求,以及對於自己身為女性的定義,來選擇順服或者抵抗制體制。換言之,探討性別在工作中的影響並非把女性加入分析的架構中即可,而是必須注意到女性自身也具備多元形貌,且複雜性不可忽略。
李用了香港和深圳這兩個工廠的特殊性,很精彩的呈現出和Burawoy以階級為主要軸線來解釋工廠體制的形成原因截然不同的切入方式。她強調了地方勞動市場以及性別化的社會組織,都是形塑工廠內部的治理體制形貌的重要因素。由此,李不僅建議了一種以「關係式配置」(relational setting)的角度去瞭解工廠體制的切入方式,同時也主張我們需要一種「性別化的生產政治理論」。李主張工廠體制本身就是性別化的,且性別出現在各種過程、實踐、形象和意識形態之中,同時也是在社會生活的不同快中分配權力的一種機制。也正因為如此,就像Liton的例子所指出的,即使在國家不干涉的狀況下管理階層有著很大的自主性去決定其管理策略,但是最終工廠體制的生成,還是需要跟在地的勞動市場,性別相關的社會組織纏繞在一起之後才得以成形。由此,李開闢了一條不同於Burawoy,加入了性別面向的討論途徑。
對我來說,李的這本書討論精彩且理論耙梳簡潔扼要,同時還非常有理論推進的意義。在理論的層次上,本書的貢獻在於「加入性別的層面之後,我們可以如何深化對於工廠體制的理解?」我看到的是,李以性別角度,去架接了外在社會的性別相關的社會組織如何影響到工廠內部生產政治的興成。相較於過去其他的女性主義研究者來說,對於在父權體制中的女性煮體性,有了更細緻的描繪並且給予了更多理論上的解釋力,而不再只是單純的經濟決定論式的討論。這個部分對於女性主義的工作研究,也是相當顯著的推進。
不過,在強調了地方勞動市場特性之際,李把Liton的管理階層當作了不變項,是整個分析中缺席的因素。在李的分析中,這些管理階層因為是同一批人,因此預設了他們有著相同的管理思維,而這個思維是一個沒有中心思想,”Be Water”的狀態,由是可以因地制宜的讓地方因素形構工廠體制。這樣的分析路徑不論是和我再田野中看到的,或者是McKay對菲律賓的討論,都呈現出很不同的形貌。換言之,我覺得李強調了性別的重要性的同時,低估了,或者說,將資方對於工廠體制可能造成的影響存而不論了。
這樣的切入,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依循了女性主義研究者的進路,亦即強調在地性別意識形態、社會組織、分工、刻板印象對廠內勞動控制策略造成的影響。頂多加上經理本身的性別觀點,由此共構了勞動控制策略這樣的一套分析架構。但是,這不禁讓人想要問,加入性別的層面之後,就真的窮盡了所有影響勞動控制的因素了嗎?資方的角色就真的如流水一般的無形且隨遇而安嗎?這是李未處理而有待探問的一些問題。